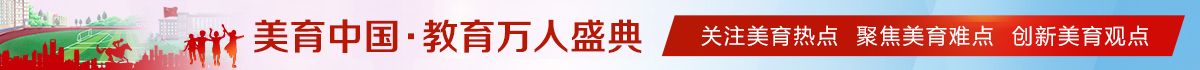20世纪以来的西方现代美学呈现了多元、多变的发展轨迹,出现了种种“转向”,如“非理性转向”、“心理学转向”、“语言论转向”、“文化研究转向”等。但迄今为止,人们却忽视了其中另一种重要的转向即“美育转向”――在由古典形态的对美的抽象思考转为对美与人生关系的探索、由哲学美学转到人生美学的过程中,美育在西方现代美学、特别是现代人文主义美学中成了一个前沿话题。

这一转向并非偶然,而有其现实的社会根源:整个20世纪,科技经历了由机械化到电子化再到信息化的发展,经济活动由工业时代逐步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教育则经历了从世纪初以测试主义为标志的应试教育泛滥到20世纪后半叶素质教育受到广泛重视的转变。这种社会的巨变,使得包括想像力在内的人的审美力发展问题显现出从未有过的重要性,美育的地位也由此得以凸现。此外,社会现代化的步伐,同时也带来了工具理性膨胀、市场拜物盛行与心理疾患蔓延等各种弊端。而这些弊端的共同点,便集中体现为人文精神的缺失。因此,对现代化进程中人文精神的补缺便成为十分紧迫的当代课题。而美育作为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实施人文精神补缺的重要途径。因此,西方现代美学的“美育转向”正应和了时代的需要。

具体说来,西方现代美学的“美育转向”,是以康德、席勒为其开端的。康德在其哲学体系中完成了“自然向人的生成”,使美学成为培养具有高尚道德的人的中介环节,第一次把美学由认识论转到价值论、由纯粹思辨转到人生境界的提升。这就是康德为西方现代美学的“美育转向”所开辟的道路。而席勒“基于康德的基本原则”,将美育界定在情感教育范围并明确提出“要使感性的人成为理性的人,除了首先使他成为审美的人,没有其他途径”[1]。特别可贵的是,席勒的思想体现了鲜明的现代色彩,包含了对于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异化”现象的忧虑与试图消除的内容。可以说,康德与席勒为西方现代美学的“美育转向”奠定了基本方向。
其后,叔本华、尼采具有更加鲜明的现代性。他们以“生命意志”、“强力意志”为武器,彻底否定了西方的理性主义传统,倡导“人生艺术化”,把审美与艺术提到世界第一要义的本体论高度。